无机水磨石地坪
节能环保 高装饰性 整体无缝
咨询热线:
1318897377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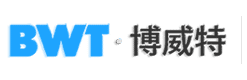
无机水磨石地坪
节能环保 高装饰性 整体无缝
13188973775
发布时间:1970-01-01 编辑作者:8868体育app首页 浏览次数:1 文章来源:企业新闻
十二年后的我,活成了一根厂里的顶梁柱,不是说我多重要,而是我像柱子一样,每天杵在同一个位置,纹丝不动。
我在一家生产轴承的国企里做质检,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卡尺和眼睛,去分辨那些铁疙瘩零点零几毫米的差别。
日子过得像厂里那台老冲床,哐当,哐当,每一声都和前一声一模一样,听久了,也就忘了时间。
她人不错,就是嘴碎,总觉得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,经常指着电视上那些创业成功的胖子对我说:
“陈默,你看看人家,再看看你。当年你要是脑子活络点,咱们现在也不用为了孩子上哪个幼儿园抠抠搜搜。”

那是我爹妈一辈子种地攒下的钱,是我准备结婚的钱,是我以为的未来的基石。可这块基石,被我的战友,我睡了两年上下铺的兄弟马奎,轻飘飘地借走了。
我信了。我看着他那双因为激动而布满血丝的眼睛,想起了在部队里,他背着发高烧的我,在泥地里走了二十里山路。
我想起了我们俩躲在猪圈后面,抽同一根烟,他说退伍了要干一番大事业,开一家全中国最大的面馆。
他走了,就再也没回来。电话从一开始的“正在通话中”,变成了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。
我没结成婚,未婚妻的妈说:“一个能把结婚钱随随便便借给别人的人,靠不住。”
我把马奎这个人,连同那六万块钱,埋进了心里最深的地方,用十二年的沉默,给他砌了一座坟。
有时候在厂里,看着那些飞速旋转的轴承,我会想,马奎现在在哪儿?是不是真的像他爹妈说的那样,死在了哪个没人认识的角落?又或者,他真的成功了,成了电视上那种油头粉面的胖子,早就忘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叫陈默的傻子。
想得多了,也就麻木了。就像手上的老茧,刚开始磨破皮的时候疼,时间长了,再用砂纸搓,也没什么感觉。
我和林晓吵架,她骂我窝囊废,我就想,对,我就是个窝囊废,一个被六万块钱就压垮了的窝囊废。这种承认让我感到一种病态的轻松。
上面是打印的我的名字和地址,寄件人那一栏,印着一行烫金的小字:君诚律师事务所。
我捏着那封信,感觉它不像信,像一块冰,凉气顺着我的指尖,一路钻进了我的骨头缝里。

一路上的风比平时要冷,吹得我脸上发紧。电瓶车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,像是在嘲笑我的紧张。
我把信掏出来,放在客厅的茶几上,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凉白开,一口气灌了下去。
我反复看着那个信封,上面的“陈默先生”四个字,像是四个黑色的洞,要把我吸进去。
最后,一个尘封了十二年的名字,像水鬼一样,从我记忆的深潭里浮了上来:马奎。
十二年了,他终于出现了?可为什么是通过律师?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各种狗血的剧情。他是否在外面混得很惨,欠了一债,现在债主找到了我这个“原始债权人”?还是说,他得了什么绝症,临死前良心发现,让律师来处理这笔烂账?可他怎么会知道我现在住在这里?
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,手心里的汗把信封都浸得有些软了。我害怕,我怕打开它,看到的是我不想看到的东西。
比如一张催款单,上面写着马奎欠了别人一百万,因为我是他唯一的联系人,所以要我承担连带责任。或者更糟,是一份死亡通知,告诉我马奎客死他乡,让我去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替他收尸。
在街上,我一眼认出他,冲上去揪住他的领子,问他那六万块钱呢?为什么像狗一样消失了?他或者跪地求饶,或者满脸不屑。无论哪种,我都能在他脸上狠狠地来上一拳。
它像一个判决书,而我,是被告。我的罪名,可能就是十二年前的那次愚蠢的信任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,又长长地吐出来,仿佛要把胸口积攒了十二年的浊气都吐干净。死就死吧,一颗脑袋掉了,碗大个疤。我活得这么窝囊,也不怕再多一件窝囊事。我用微微颤抖的手,沿着信封的边,一点一点,极其缓慢地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纸张撕裂的声音,在抽油烟机的噪音里,显得格外清晰,像是啥东西在我心里断掉了。

纸很厚,A4大小,带着一股高级打印纸特有的清香,和我平时在厂里用的那种再生纸完全不同。我闭上眼睛,心里默念,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。
那是一行加粗的黑体字:“关于‘寻味九州餐饮集团’原始股东陈默先生股权确认及价值重估的律师函”。
寻味九州?我没听过。原始股东?我连股票账户都没有。股权确认?价值重估?这都什么跟什么?我甚至怀疑这信是不是送错了,可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:陈默。
我的心跳得像被狗撵的兔子,砰砰砰,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我有一种极其荒谬的感觉,就像一个穷了一辈子的人,突然有人告诉他,其实他是某个失落王国的王子。
我们是君诚律师事务所,受‘寻味九州餐饮集团’及其创始人马奎先生的委托,特此向您致函。”
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,我强迫自己稳定心神,继续读下去。接下来的一段话,让我彻底停止了思考。
“根据公司创始章程及原始股东协议记载,您作为公司的天使投资人及创始股东之一,持有公司30%的原始股份。该股份权益由您于2012年投入的6万元人民币创始资金转化而来。”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记得,十二年前,马奎在酒桌上喝多了,是拍着胸脯说过“等我发了,你就是股东”,我只当那是酒话,是兄弟间吹牛的玩笑。
他给我写的借条上,清清楚楚写的是“借款陆万圆整”,就没有什么股份协议。
马奎发达了,但他不想还我那六万块钱,所以弄出这么个复杂的名堂来恶心我?用一个虚无缥缥的“股东”身份,来抵消一笔实实在在的债务?
愤怒和困惑交织在一起,像两只手,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几乎要把那几张纸给捏碎。
“现‘寻味九州餐饮集团’已完成C轮融资,并真正开始启动上市流程。根据相关法规及股东协议,需要对您的股权进行确认与价值重估。经国内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,您所持有的30%股份,目前市场估值约为人民币……”
我反复看了三遍,确认不是六十万,也不是六百万,是六千万。那一长串的“0”,像一排排黑洞,旋转着,要把我的灵魂都吸进去。
我不是惊喜,不是狂喜,也不是激动。我就是傻了,彻头彻尾的傻了。我的大脑像一台被病毒感染的电脑,彻底死机,蓝屏了。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,我听不到抽油烟机的声音,听不到窗外的车流声,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疯狂的跳动,和血液冲刷耳膜的嗡嗡声。

林晓端着一盘炒好的青菜从厨房出来,看到我像个木雕一样坐在沙发上,地上的纸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她把盘子往桌上一放,盘子和桌面碰撞发出“当”的一声脆响,把我惊得一哆嗦。
“你这是怎么了?丢了魂一样。”她弯腰捡起地上的律师函,嘴里还在埋怨,“什么破通知,看把你吓得。”
我没说话,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她。我想告诉她,那不是破通知,那是炸弹。可我的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,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
林晓的目光落在纸上,起初是不耐烦地扫了一眼,然后,她的表情凝固了。她的眼睛一点点睁大,嘴巴也微微张开,手里的那几张纸,开始像我刚才一样,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“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……”她竟然一个数位一个数位地念了出来,声音带着一种不真实的颤音,“六……六千万?”
她的话点醒了我。对,诈骗!这肯定是诈骗!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?一个消失了十二年的“骗子”,突然变成了财神爷,还给我送钱?这比我在厂里质检出一颗纯金的轴承还要荒谬。
君诚律师事务所,我在手机上飞快地搜索了一下,立刻跳出了官方网站和百科介绍。
“餐饮界黑马‘寻味九州’完成C轮融资,估值超二十亿!”“专访寻味九州创始人马奎:从后厨小工到餐饮巨头的传奇之路。”“揭秘寻味九州:一家不做加盟的‘笨’公司如何席卷全国。”
我点开那篇专访,一张高清的照片弹了出来。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脸上带着商业精英特有的自信微笑。他瘦了,也黑了,眉宇间多了几分沧桑和凌厉,但那张脸,那双眼睛,化成灰我都认识。
照片旁边的文字记录着他的神话:十二年前,他身无分文来到南方,在饭店后厨洗了三年盘子,后来用全部积蓄开了个小面馆,凭借独特的口味和经营方式,一步步发展壮大,如今,“寻味九州”在全国拥有三百多家直营店,是餐饮行业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头。
我看着照片上那个意气风发的马奎,再看看自己因为常年握卡尺而布满老茧的手,和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,一种巨大的、难以言喻的荒诞感淹没了我。
我们曾经睡在同一张上下铺,吃同一锅饭,穿着同样肥大的军装,对着同一个月亮发誓要出人头地。十二年后,他站在了云端,而我,还陷在泥里。
林晓也看到了那些新闻,她一把夺过我的手机,反复确认着那些报道,然后又拿起律师函,两相对比。
“真的又怎么样?”我突然爆发了,冲着她吼道,“他马奎成了亿万富翁,关我屁事!他欠我六万块钱,欠了我十二年!现在弄个什么狗份来羞辱我?他啥意思!”
我的愤怒来得莫名其妙,却又理直气壮。这六千万像一座山,突然压在了我的生活里,把我原本虽然贫瘠但还算平静的土地砸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。
林晓也愣住了,她大概从没见过我发这么大的火。她呆呆地看着我,然后,眼圈慢慢红了。
“你吼什么……”她带着哭腔说,“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我就是……太吓人了……”
客厅里一片死寂,只有我们俩粗重的呼吸声。那封律师函还躺在茶几上,那串“60,000,000”的数字,在昏暗的灯光下,像一个巨大的、黑色的嘲讽。

那一晚,我和林晓谁都没睡着。我们俩像两具僵尸,并排躺在床上,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因为有点漏水,有一片黄色的水渍,形状像一幅残缺的地图。我看了它很多年,第一次觉得它那么碍眼。
我的脑子还是一团乱麻。愤怒、困惑、荒诞、还有一丝被我自己死死压抑住的、可耻的窃喜,这些情绪像一锅沸腾的粥,在我脑子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
“要不……按照信上说的,给那个律师打个电话问问?”林晓提议道,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
我沉默了。打电话,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我必须去面对这件事,面对马奎,面对那六千万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在战壕里躲了十二年的逃兵,现在突然有人告诉我,战争结束了,我成了英雄,还发了一大笔奖金。我走不出那个战壕。
第二天,我照常去上班。厂里的冲床依旧“哐当、哐当”地响,同事们依旧在说些家长里短的笑话。
我看着手里的卡尺,看着那些闪着金属光泽的轴承,它们在我眼里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。我满脑子都是那串“0”和马奎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。
我总不能告诉他们,我那个消失了十二年的战友,现在要给我六千万,而我正烦恼该不该要。他们会以为我疯了。
一整天,我都像个游魂。中午吃饭的时候,我把饭盒里的红烧肉一块一块地夹出来,排成一排,然后又一块一块地吃掉。我不清楚自己为何需要这么做。
她的理由很简单,我太“傻”,太“不靠谱”。我没有挽留。我知道,她说的是事实。
马奎消失的第三年,我认命了。我把那张写着“借款陆万圆整”的借条,折成一个小方块,塞进了一个空的茶叶罐里,再也没打开过。
我努力活成一个“靠谱”的人,一个把工资卡上交,从不乱花一分钱的丈夫和父亲。
我以为我已经把马奎给忘了。可现在我才知道,我没忘。他就像一根扎进我肉里的刺,我以为它已经和我的血肉长在了一起,不再疼痛。
他凭什么?他凭什么消失十二年,让我活得像个笑话?他又凭什么现在忽然出现,用一笔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巨款,来宣告他的成功和我的失败?
江风吹在脸上,又冷又硬。我把烟头狠狠地扔进江里,看着它闪着一点红光,迅速熄灭,沉没。
回到家,林晓已经做好了饭,但没动筷子,显然是在等我。她看到我通红的眼睛,什么也没说,只是默默地给我盛了一碗饭。
“打吧。”她说,语气很平静,“是真是假,是好是坏,总得有个说法。躲是躲不过去的。”
我看着她,突然觉得,这个平时只知道唠叨和抱怨的女人,在关键时刻,比我这个当过兵的男人还要有主意。
我拿起手机,按照律师函上的电话,按下了那个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会拨打的号码。

“陈默先生,是吗?”对方的语气没有丝毫波澜,“马先生已经交代过了。我们从始至终在等您的电线
在我记忆里,他永远是那个在训练场上被汗水浸透了背心,咧着嘴对我笑的“老马”,是那个和我勾肩搭背,说“阿默,以后咱俩一块儿干”的马奎。
“是的,马奎先生。”电话那头的女律师声音冷静得像一台机器,“陈先生,关于律师函里的内容,您应该已经看过了。我们应该和您预约一个时间,当面进行股权文件的签署和确认。同时,马先生也希望能和您见一面。”
这三个字像三根针,扎在我的心上。我该用什么表情去见他?是愤怒地质问,还是尴尬地寒暄?或者,像个小丑一样,对他表示感谢?感谢他十二年后,终于想起了我这个被他遗忘在角落里的“股东”?
“这是马先生本人的意愿。他说,有些事情,他必须当面向您解释清楚。”女律师的语气依旧平淡,但似乎多了一丝人情味,“陈先生,我们理解这件事可能对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。您可优先考虑一下,决定好时间后随时保持联系我。”
“去见见吧。”她说,“不管怎么样,你们总是战友。把话说开了,不管这钱你要不要,心里这个结,总得解开。”
我转过头,看着她。灯光下,我能看清她眼角的细纹和鬓角的一丝白发。这些年,她跟着我这个“窝囊废”,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如果这六千万是真的,那我们的生活……
我把那个装有借条的茶叶罐翻了出来,打开它,那张被我捏得皱巴巴的借条静静地躺在里面。
当年马奎到底是怎么说的?他真的说过“给你股份”这种话吗?还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?时间太久了,久到记忆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
门口的侍者看到我从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上下来,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令的轻视。

包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坐在那张柔软得不像话的椅子上,感觉自己像个误闯了宫殿的乞丐。我看着桌上精致的骨瓷茶杯,不敢去碰。
8868体育官方网站app首页登录 版权所有 备案号: 鲁ICP备20063598号-4